尴尬是生活开玩笑 世界杯带出来的那些翻译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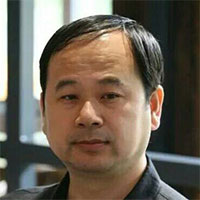
都说,翻译是一个注定失败的职业。因为,翻译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新鲜事物的挑战。当然,翻译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充满未知和新奇的职业:两种文化的碰撞,总会在情绪最激动时达到顶峰,而生活这位艺术大师,也每每在这个时候把翻译放到一个尴尬的位置。
世界杯,让我再次体味俄语翻译乐趣之际,也记起了职业生涯中的几次尴尬。
世界杯期间,在莫斯科采访完毕,我和年轻的丁丁老师乘坐俄罗斯帅叔叔科里亚的商务车回宾馆。路上聊起战斗民族的火爆脾气,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丁丁老师,突然异想天开地说:“俄罗斯人如何骂人呀,教我一句呗?!”
工作完成的挺顺利,心情不错,所以,一时兴起,就小声教了他两句连在一起的俄语;一句类似中国国骂的口头语,一句绝对的俄语骂人挺狠的话!
真的没有想到,丁丁老师竟然大声念了出来!而且,还是在不断重复地念,大有想把其背下来的劲头!
我当时真是尴尬极了:他可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扭头大声念出来的时候,脸可是正对着科里亚大叔的!
不过,无论我怎么想,一幅绝对疯狂的画面还是出现了:丁丁老师一脸严肃地骂一句,稍懂两句汉语的科里亚大叔,就忍不住哈哈大笑着用俄语夸赞一句“对”!丁丁老师不停地骂,科里亚就不停地哈哈大笑着连声说“对,对!”!
还好,丁丁老师绝顶聪明,学的那两句话非常标准,科里亚才没有给他纠音!
其实,我知道,对于年轻人而言,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最容易掌握的表达方式就是讲粗话,而每个人听到老外能骂出本国经典国骂时,第一反应也绝对不是生气而是惊奇。
记得,N年前,我对俄罗斯海员讲的第一句话也是粗话。那是在大连接待一艘俄国海船,船长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妈的,这么嫩,听得懂俄语吗?”非常恼火的我忍不住大声说道:“你妈的,谁告诉你我听不懂俄语?”船长先是一愣,接着哈哈大笑,于是,接下来的工作异常顺利!
专家公寓新来了一批外国专家。因为他们要在中国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有的人就带上了家属。于是,本来非常安静的公寓里,多了三个吵吵闹闹、金发碧眼的小家伙:两个男孩,九岁的谢尔盖,六岁的安德烈;女孩娜佳四岁。
三个天真可爱的小家伙,立即得到了中方服务人员的一致欢迎。
不到一天的时间,三个小家伙,尤其是谢尔盖和安德列,就和我这位喜欢孩子的生活翻译混熟了。
吃过晚饭后,闲来无事,带着三个小家伙开始在草坪上嬉戏,本来正开心地看着他们在那里大声吵闹,一股属于嫉妒的无名之火却突然窜了上来:他哥的,俄语我都学了有十个年头了,但讲得还不如这几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流利!一个恶作剧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试试小时候逗更小的孩子打架时的这个招术!
结果,两个男孩子被我一本正经地叫到了身旁:
“谢尔盖!安德列!你们两个人,谁厉害!”
没等我话音落地,谢尔盖早已一个箭步蹿到了比他矮一个头的安德列身前,拦腰将对方抱起——并重重地摔在地上。
原以为会听到一阵争吵声的我,只到这时才听到谢尔盖一个响高的回答:我!
当然,给他伴奏的是安德列同样响亮的哭声,以及我立即就去买冰淇淋的许诺声。
在品味中国冷饮的同时,三个小家伙也在不自觉地适应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陌生的语言——公寓里除了翻译,所有的中国人和他们交流时,全是用的汉语。尽管一些手势是国际通用的,但汉语还是最先成为了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尽管金大侠帐下的韦都统早已证明,俄语中的粗话已贫乏至极,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多么博大精深, 似乎也真没必要让俄国人从这面来领略我中华语言的风采。因此,当公寓里出现三个小老外之后,我开始告诫年轻的服务员和警卫们不要教小孩子们说脏话。
但真理就是真理,放之四海确实皆准:即便是到了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还没用完两个星期,小安德列就已经学会了两三个标准的普通话贬义词,甚至还学了一两句连我都听不懂的江南方言——相信那些也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没办法,优美的中国语言,到了小安德列嘴里,只能是那种恶心人的味了。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听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嘴里冒出标准的中国国骂时,第一反应却也是哈哈大笑,第二反应就是回骂一句。于是,少不更事的安德列更是大受鼓舞,骂人话越学越多。
这天,开饭时间到了,公寓的领导却在饭厅外面将服务人员集合起来罗罗嗦嗦地训起话来。
强打精神、做出毕恭毕敬样子聆听领导训示的我,虽然在努力压制肚子提出的有声抗议,但眼角的余光还是发现:小安德列突然出现在了我们领导的身后。见他冲我挤了挤眼睛,我才想起曾答应他:饭后陪他去旁边的公园玩。
领导的讲话,并没有因为安德列的出现而中断,我只好冲小家伙挤了挤眼睛。
也许,他也明白,正是因为领导不让我们吃饭才耽误了他的大事;也许,他想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好好地表现一下,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安德列突然指着在众人面前讲话的领导破口大骂起来——而且还是标准的普通话夹杂纯正的当地方言!
当然,安德列想听轰笑声的预谋肯定是不会得逞的,但我们这些听训话之人却也为之付出了绝大的努力——个个把脸憋得通红:搞得自己也跟个领导似的,不过,人家真正领导的脸却是气红的!
八小时之外,电话响了:公司一位领导要在公寓和专家们谈点事情。恶狠狠地扔下电视遥控器,我非常不情愿、但却是快速地冲下了宿舍楼。
老远,就看见安德列正在和那位领导站在会议室外的草地上,互相指着鼻子说些什么。
当我走近时,领导早已恢复了一本正经、虎视眈眈的样子:“已经通知外国专家了吧?!”
我刚点了点头,还没来得开口讲话,小安德列已经抬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叫道:“住!住!”
我蒙了,一下子愣在了那里!俄语里哪来的这个单音节词?什么意思?
领导将头转向了另外一方向,不再看我,而小安德列却更加兴奋地大声叫了起来:“住!住!”
看到领导脸部抽搐的肌肉,想象他那一脸的坏笑,我终于明白了:小安德列是在大声呼唤一种动物的名称!
“谢尔盖!”恼怒的我大声喝道。
小安德列转身就跑,跑的比小兔子还快。
“咦,这个小家伙不是叫安德列吗?”领导转回头来,一脸的惊奇。
“他淘气时,我向来让谢尔盖揍他。”
翻译水平的高低,不在于他掌握他词汇的多少,而在于他反应速度的快慢。不过,有时反应速度太快了,效果却是意想不到的:
陪同公司两位领导游览莫斯科俯首山,大家坐在一条长椅上略事休息之时,一条可爱的小板凳狗突然出现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很想仔细欣赏一下其精致之处的两位领导,尽管拿出了国内唤狗的一切招术——甚至都试过了招猪的“喽喽”法术,但小狗却仍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也许他觉得这些不停地口出怪音的老外有趣极了?虽然我也知道在俄罗斯随便逗别人的狗比随便逗人家大姑娘还招人烦,但仔细观察四周没发现狗主人之后,我决定卖弄一下自己的本事:对着小狗轻轻地用俄语说了声——过来!
没出我所料:小狗真的摇头摆尾地走到了我面前,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却是哈哈大笑着的领导无意间讲出的一句话:狗懂俄语!
真想上去狠狠地踹他一脚,但没敢,又想踹小狗一脚,但没好意思。
有一次,随公司的代表团访问小安德列的家乡——彼得堡。
晚上,独自坐在宾馆附近森林公园的长椅上,面对芬兰湾,无聊地观看波罗的海的海鸥争食。突然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代表团的两位团长也出来散步了,本来想立即站起来打个招呼,但两位团长因为没有发现我所以仍在进行的谈话却让我又坐了下来:
“李总,你说我们那个张翻译多差,我上午讲了一句话,他译了十来句也没让俄国人明白是什么意思!”
“行了,张翻译已经不错了,刚才酒席宴上,我讲了有十来句,人家李翻译一句俄语就给我交待了!”
当然,做翻译,不能总是尴尬,有时,也会让别人尴尬一回!
在莫斯科报道世界杯期间,由于所住酒店是国际足联征用专供媒体人使用的酒店,因此,不仅来来往往的旅客人都在讲英语,就连坐在酒店前台后面的俄罗斯小姑娘、小伙子也是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英语绝对成为了这座酒店的通用语言,以至于我这位俄语翻译,每天在前台给自己的房门卡充磁时,基本上也是顺着人家的话音报报上几个英文数字:这家宾馆规定,无论你在此住多少天,房门卡就给你充一天的磁,所以,即使你在这里住上四十多天,也必须天天到前台报房间号充磁。
这天,坐在大堂等一位朋友下楼。突然,就看到,前台小伙子送走一位客人之后,很是意味深长地对旁边的迎宾小哥说道:“中国人很狡猾!”
我马上高声应道:“俄罗斯人很聪明!”
他两个先是愣了一下——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想到旁边坐了一个懂俄语的中国人,接着两人都尴尬了,绝对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神情,前台一个大小伙子,竟然也脸红了!
